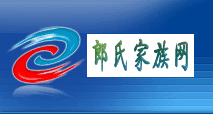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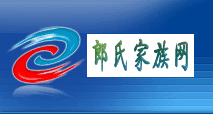 |
|
||||||||||||||
| | 网站首页 | 宗支世系 | 郎氏渊源 | 郎氏祠堂 | 宗亲总会 | 郎氏基金 | 郎氏荣耀 | 活动掠影 | 雁过留声 | | ||
|
||
|
|||||
| 江南老谱考证报告(一) | |||||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镇雄郎氏的BLOG 点击数:959 更新时间:2008/12/17  |
|||||
江南老谱考证报告(一)理事会: 遵照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夏历八月十三日)在镇雄召开的全体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简称镇雄会议)精神,我们考证组于二〇〇七年十一月20日(夏历十月十一日)开始对我郎氏江南老谱进行考证,历时118天,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20日。上午,我们全体考证组成员进城集中,首先进行了初步分工,各自明确职责。然后确定行程路线。其次,确定到婺源后落脚点是清华镇,这是根据之前郎革成先生在与我们通话中提出的要求而定的。再其次是确定出发前发给郎革成先生短信的内容以及与郎革成先生联系的方法步骤。最后,在进一步明确会议交办三个任务基础上,还对其它要办的事情进行梳理并作好记录,这些事归纳起来主要有十三点: 1、我们把从神保公纪念碑、凤公、文公武公以及献公夫人墓上所取的土带回老家,还带上香蜡钱纸,投放在老家的土地上并进行祭祀,表示神保公他们及他们的后裔不忘自己的根,要报本尊宗。同时还要从老家取土携带回撒其上,表示故土难忘。当然这要尊重老家的风俗习惯,征得老家宗台同意,才能实施。 2、祭祀祖先坟墓。 3、瞻仰28世祖敬公当年办公的老县衙及敬公笔下的九井十三巷。 4、瞻仰并祭祀宗祠。 5、拜访45世祖盛公择幽而居的晓湾。 6、收集寻找历代祖像。 7、打访并拜望老家家门集居的村寨。 8、收集了解宏声公当年抄录老谱的情况,并对其抄录的版本进行核实。 9、收集了解芳声公当年在景德镇为官的情况。 10、查查在老家有无神保公和能公的墓。 11、就郎文杰先生首倡修《郎氏通谱》一事交换意见。 12、查查我们这里的前二十代排行在老家的谱书上有无记载。 13、适当游览老家的名胜古迹和湖光山色。 代理事长郎德启对这次考证工作非常重视,亲自到场作了指示,反复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取证要实,分析要细,判断要正确,不能草率行事。他还把亲自出具的《介绍信》重新找电脑打印,以示庄重,足见其对此项工作的重视。他还亲自送我们上了下午四点去贵阳的班车。他目送我们走了好远好远,这时我们感到,那哪里是代理事长,是全体理事会成员,不,那是神保公后裔两万多双殷切期盼的眼睛在关注着我们,我们很感动,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在车上,我们收到了郎革成先生的短信,他得知我们已经出发,要求我们到清华后就住“锦水饭店”,我们记住了。 二十一日。天未明,我们平安地到达贵阳,郎学友等贵阳家门,特邀我们在一家很繁华的具有民族风味的餐馆共进晚餐。晚上十一点零四分,我们登上了去江西上饶的火车。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路顺风,晚上到达了上饶。 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我们便乘上去婺源的汽车。这时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大有归心似箭的感觉。到了婺源县城一下汽车,就打车前往清华,急切地想尽快与郎革成先生见面。到了清华后,就在沱口人郎锦水开的“浙源饭店”住下。郎锦水50岁左右,曾经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他们一家对对我们特别热情。吃了午饭,我们就急急地赶到距清华22公里的沱口,与郎革成先生会了面。 郎革成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头戴鸭舌帽,头脑灵活,反应迅速,目光敏锐,应变自如,说话响亮,行动敏捷,看上去简直不像一个80高龄的老人。我们向他呈上了代理事长出具的《介绍信》,并出示了各自的身份证后,他便拿出珍藏的《中山郎氏宗谱》(民国五年版)给我们查阅。我们迅速找到神保公名下的有关记载,赫然发现不仅神保公与能公之间有寿魁公、瓒公两代的记载,而且还记载得有神保公原配夫人吴氏所出的寿诚公一支。同时也记载了能公以下直到声字辈的部分内容。我们把我们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地谱书的记载情况向革成先生作了介绍,觉得出入太大,问题严重,革成先生则认为《中山郎氏宗谱》(民国五年版)的记载是正确的,我们因刚刚接触问题,胸中无数,不好说什么。只好把话题转到其他方面。革成先生告诉我们,屏山的宗祠在一九九五年被烧毁了,所有的东西全部化为灰烬,真是太可惜了。他曾倡导修复,可支持者不多。革成先生还说:“清华寨山下,是我郎氏的集居地,神保公就是从那儿出走的。那里还有宗祠,不过已经损坏了,你们可以去看看。”我们听了很高兴,与革成先生约定好明天早上他到清华与我们正式会面后,便急忙赶回清华去拜访寨山下的宗台。 寨山下与清华镇街头只相距一条很宽的河,河上架着木板桥。我们刚到村口便遇着一个中年人,他叫郎元生,70世,我们说明来意后,他很热情,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儿,就带我们去瞻仰宗祠。宗祠只剩下墙圈圈了,大门很高,大门顶上“郎氏宗祠”四个大字清晰可见,走进去觉得空间相当大,石墙完好,地上尽是瓦砾,左后面有一道后门。我们没有实际丈量,只觉得好宽好高,同时也发现宗祠基址没有任何人占据。我们问郎元生:“宗祠墙圈还在,修复恐怕不难,你们有修复的打算吗?”他笑笑说:“现在力量单薄得很,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们根据谱书的记载,统计好各处的祖坟数,询问这些坟是否还在。郎元生仔细看了我们的笔记本说:“其它地方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东山下倒是有三所坟,我亲自见到过,不过究竟是不是你们要找的祖坟我就不知道了。我带你们去看看吧。”说完他就拿起镰刀带着我们向东山下奔去。那山草木旺盛,郎元生很快就消失在丛林中,由于没有路径,我们艰难地攀援而上,好不容易追上郎元生时,他早已经在三所坟的面前等着我们了。我们仔细辨认碑迹,有一所墓主是郎廷友,另一所是郎胡氏的墓,从孝名来推断,应当是郎廷友的母亲的墓,第三所是郎廷友的祖父的墓。看来都不是我们所寻找的祖坟,但它毕竟是郎氏的祖坟,我们都分别祭拜了。只是因严禁烟火,没有烧香烧纸罢了。返回的途中,我们发现有些铺路石上刻有文字,便仔细辨认,或许是我们正需要寻找的东西呢,可惜都不是。 当天晚上郎元生与郎社保来到我们的住处,我们便出示随身携带的谱书给他们看。他们翻到序的部分仔细阅读后说,老谱他们都看过,和这上面的内容是一样的。我们说这谱是两百多年前从这里抄录去的。他们问我们走了多少路程,我们说从镇雄县城起到清华止有四千里。他们感叹地说:“真不容易啊!”当谈到婺源郎姓分布情况时,他们说,集居地就是沱口和寨山下这两处。沱口有300人,寨山下只有21户,100人。我们又再次提起寨山下宗祠的修复问题时,他们说,大多数的人都迁走了,仅凭这百十来口人难以如愿。话题转到老家山清水秀,地灵人杰时,他们高兴地说,江泽民主席就是婺源人,他曾来过婺源,一下车就说:“父老乡亲们好!”吃饭时又说:“还是家乡的菜好吃!”他们说,自从江主席来过,婺源全县的公路都基本上铺成柏油路了。他们还说,胡锦涛总书记也是婺源人。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后来大家又唠了一些家常,各自介绍了身份及家庭情况。郎社保,1948年3月生,70世,有二男一女,现已丧偶,在寨山下独居。他身材魁梧,轻言细语,热情厚道,临别,他给我们打招呼:“明天,我请你们吃顿饭,时间定在上午11点。”我们推辞,他说:“你们几千里路来到老家,怎么连饭都不吃一顿呢?我如果到了你们那里,同样也要吃饭。”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郎革成先生来到我们的住处。同他一起来的还有郎社保先生的长子郎斌。郎斌是去找郎革成先生看病的,获悉后特来与我们会面的。会面时,大家自谦普通话说得不标准,不过只要能表达意义就行了。革成先生把郎斌介绍给我们,我们便与郎斌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后来郎社保先生也来了,大家一起商定了考证日程安排:下午——游览彩虹大桥,逛逛唐代老街;25日——因革成先生要到城里参加一个文化团体会议,不能参与我们的活动,根据革成先生的建议,决定先去江湾瞻仰江主席家宗祠,再到县博物馆查阅有关资料。郎斌说,到了江湾就给他电话,他陪我们一起游览;26日——先去拜望晓湾,然后返回沱口拜读《中山郎氏宗谱》(民国五年版),再去祭祀屏山的宗祠,最后返回清华祭祀寨山下的宗祠;27日——上午,革成先生带《中山郎氏宗谱》(民国五年版)到清华,我们对有关资料进行复印。下午,进行合影留念。日程安排完毕,我们又把带土、取土的想法提了出来,得到了老家宗台的首肯。接着,我们又出示随身携带的香蜡钱纸说:“这是我们当地使用的祭品,不知与老家的祭品是否一样,能不能使用?”宗台仔细看了看说:“香蜡是一样的,钱纸不同。不过,用你们带来的祭品祭祀最好。”当即议定:在两座宗祠、清华街头、晓湾等四处祭祀并撒放带来的泥土,同时又取上泥土带上。 11点,我们便随郎社保先生到了一家餐馆共进午餐。席间,我们把镇雄县郎氏家族理事会如何获取郎启波传来的信息,如何重视,如何研究,如何决定考证并派遣我们到老家来的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宗台们对理事会的做法大加赞赏。 饭后,我们就开始按商定的日程行事了。 社保和革成二位先生陪我们一起游览了彩虹桥。彩虹桥是清华镇的一大名胜,《闪闪的红星》等好多电影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桥面全是木料结构,造型优美,色彩斑斓,远远望去,犹如七彩长虹横跨在波光粼粼的河水之上,真是名不虚传。水磨房里,水车在车,石磨在磨,我们为这繁忙的景象所吸引,但是最吸引我们的是悬挂着的革成先生所撰的那副对联: 石磨无言,磨去千年岁月; 水车有幸,车来万里宾朋。 它把我们的思维从“好玩”这一表象引入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回味历史,惊羡现实。“磨去”、“车来”真是神来之笔。 游完了彩虹桥,我们又游游览了唐代老街。这条具有千年历史的老街,是饶州通往徽州的交通要道。路面不宽,两边都是高墙,每隔一段距离,就在一道大门,并标注得有巷名。每一个巷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住宅区,从外向纵深望去,感觉区域不小,住的人户也不会少。两边的巷口不是对称的,好象是故意错开似的。开始,我们还对巷名逐一记录,后来发现巷口太多,可能不只十三巷,也就没记了。革成先生的知名度很高,与他打招呼的人不少,当然,大多数的人认识他,他却不一定认识人家。我们常发现有些人与他擦肩而过后,悄声议论:“这不是郎医师吗?”可他似乎没有听见。革成先生偶尔走进巷口,邀约不少人出来与我们一起游览。他们都是老年人,并且都是文墨之士,得知我们回祖籍观光,很高兴地与我们一起边走边交谈。革成先生指着一个巷口告诉我们:“胡锦涛总书记家就是从这里迁出去的。”我们便向巷口内注目好久。社保先生还特意领我们到一个小院参观一口古井。这口古井不知井名,已经废弃不用了,但保存完好,只是井口出土部分有些残缺。我们仔细观看了一会,并猜测说,这恐怕就是敬公笔下的九井之一了,不知其它的八井是否还在?社保、革成二先生都说,没有了。由于老县衙已不复存在,我们瞻仰敬公当年的衙门的愿望便落了空。我们还参观了方塘,这是岳飞当年率领士兵挖掘的。整个唐代老街,一派古色古香的风味,没有一点现代建筑夹杂其间。徜徉在唐代老街,我们仿佛回到了一千年前的唐代。唐代老街,我们觉得好长,走了一个多小时。 游完唐代老街,在返回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聊: 郎革成:理事会在给我的信中,引用了郎人豪的序,序中提到的郎熙臣就是我的父亲。 我们:啊?是你的父亲?这太巧了! 郎革成:不过,那时还没有解放,我的父亲不是什么宗祠总管,而是屏山小学的名誉校长。我父亲团了一堂学,到外地请来了三位先生任教,人们就称他为名誉校长,其实是不管事的。 我们:不管怎么说,他在族中说话是管用的。 郎社保:(指郎革成)他家是地主。 我们:这是肯定的,不然…… 郎革成:序中提到的那封信是我代我父亲回的。 我们:什么?那封信是你的亲笔,这不是又更巧了吗? 郎革成:不过,那来信的不是叫郎人豪,而是叫郎什么英的。 我们:郎毓英。 郎革成:对对,就叫郎毓英,字写得满好的。自从我回过他的信后,就再以没有收到他的来信。走,我们看看郎人豪的序去。 回到住处,我们打开镇雄《郎氏族谱》找到郎人豪的序递给革成先生,他一看到简介部分的开头:“郎人豪,字毓英……”便说:“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接着,他仔细看了序的全文后,指出序中所引的江南排行错了三个字。我们立即请他在谱书上作了订正。随后,革成先生说,他要回去为明天进城开会做些准备。社保先生也说,后天他本来是要陪我们一起去晓湾的,可最近几天有要事要办,就不能奉陪了。当下我们与革成先生约定后天早上在晓湾见,二位先生就告辞了。 晚上。我们打开革成先生留下的笔记本,找到有关神保公以后的资料摘录,认真研读,先找准两地谱书记载的出入之处,再深入分析,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为了表述方便,我们把革成先生珍藏的《中山郎氏宗谱》(民国五年版)称为民国五年版,把镇雄《郎氏族谱》称为镇雄版。两部谱书摆在我们面前,信谁的好呢?照理说,民国五年版出自老家,资历要老得多,应当具有权威性,而镇雄版是1996年才在新家出版的,权威性必然要打折扣。不过镇雄版的有关江南部分的内容也是来自老家,从乾隆47年宏声公到江南访谱来推测,其资历要老得多,这就必须先搞清楚当年宏声公到江南所抄录的版本是哪一个,再结合时代背景等因素来考察。要搞清楚版本,得先从修谱次数入手。 根据民国五年版记载,老家的谱书共修了6次,即: 第一次 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 第二次 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 第三次 清康熙戊午年(公元1678年) 第四次 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 第五次 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 第六次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 宏声公是乾隆47年(公元1782年)到达江南的,按6次修谱说,宏声公所抄录的版本应当是康熙戊午年版。不过我们又很快发现,第一次与第二次修谱之间的间隔时间是485年,跨越了两个朝代,这似乎不大可能。于是,我们根据镇雄版《谱序汇览篇》对乾隆47年(公元1782年)以前的修谱次数做了统计: 第一次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41世郎松主修。 第二次南宋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46世郎正主修。 第三次南宋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48世郎菽主修。 第四次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59世郎世荣主修。 第五次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郎庭植主修。 第六次清康熙十七戊午年(公元1678年),63世郎震主修。 第七次清康熙二十七戊辰年(公元1688年),64世郎廷芳主修。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宏声公当年到达时已经修过7次谱了。而且第七次修的谱已经问世94年。我们又从镇雄版卷二第9页查到59世郎世凤,于明万历年间续谱牒的记载。如果加上郎世凤主修的万历年版,当时江南已经是共八次修的谱了。按时间排序,万历年版(注:万历元年为公元1573年)应属第六次修谱,其余依此类推。我们揣想,距乾隆47年最近的版本就是宏声公当年抄录的版本,据此,我们可以认定这个版本就是江南64世祖郎廷芳所主修的康熙二十七年版,是具有权威性的。 但是,镇雄版不等于康熙二十七年版,它是取材于康熙二十七年版的手抄本的,并且不是宏声公当年抄录的原始手本,而是多人多次辗转抄录的手本,其可信度又打了折扣。仅凭民国五年版和镇雄版这两个版本,在没有别的老版本来参照的情况下,究竟取哪一说都是困难的。那么究竟要寻找什么版本才有用呢?通过反复分析,我们认为:嘉靖八年版、嘉靖三十年版、万历年版、康熙十七年版、康熙二十七年版,这五个版本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只要找到其中的一个版本的原版来参照,问题就好办了。当下商定:要尽量想法找到上述的原版本。 十一月二十五日。早上,我们到达了江湾镇,与郎斌通了电话。不久郎斌就与我们会面,并陪我们游览了江氏宗祠。我们看了萧何、萧衍、萧统的画像及有关源流介绍,方知江主席祖上原来是姓萧,后来才改姓江的。在永思堂的门上、柱上都悬挂着黑底金字的对联,内容和书法俱佳,令人既赏心又悦目。其中最吸引我们是那副主联,落款是郎革成: 萧国老功超诸杰,江乡贤学冠群儒,匡时经世,千秋典范长存,奕奕著勋名,足当武帅酬诗,文魁撰对; 永思堂誉播寰区,云湾里光昭列祖,鉴古观今,一代风流犹胜,煌煌开栋宇,藉答中枢垂意,元首关情。 我们边鉴赏边议论,不禁伸出大拇指,戏谑地模仿革成先生的习惯用语说道:“了不起也!” 郎斌与我们合影留念,并拒绝我们付钱。取了照片,我们便随郎斌到了一家餐馆共进午餐。是雅座,看来他早就预订好的了。郎斌举止文雅,热情厚道。席间我们各自作了介绍,从面积、人口、地形地貌、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风俗习惯、社会治安、郎氏族人一直谈到家庭情况。郎斌说,他从网上调过镇雄的资料来看过,镇雄是个大县。他还告诉我们:他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由于时代的原因,才有幸成为他们的母亲的,对他兄弟姐妹影响很大,可惜不在了。 与郎斌握别后,我们就赶到县城,随即又打车到博物馆。一看没有开馆,我们像泄了气的皮球,半天没有说话。幸好司机发问:“去哪里?”我们才商量了一下说:“去城中心看看。”于是司机把我们送到了步行街。步行街只能步行,车辆不能进入,以两座的牌坊之间的距离作为步行街的特定区域。一书“文公阙里”,一书“汪鈜少保兼太子太保……”。街道宽敞,与现代新建街道无异,两旁的建筑物顶部一律是古代建筑模式,正房部分还是现代建筑风格。街道中心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亭子,亭柱上都悬挂着黑底金字的对联,革成先生的杰作也不少。整个步行街笼罩着一种古色古香的氛围,清幽、和谐、自由、悠闲,可繁华就不敢恭维了。由于心情郁闷,我们虽然在步行街来回走了两趟,也难以领略其中的妙趣。我们又到其他地方转了转,便忧心忡忡地返回了清华。 晚上,社保先生来到我们的住处。他询问了今天我们的活动情况后,就把话题转到晓湾之行上。他建议我们最好包车去,虽然贵一点,但回来方便。我们认为:去了晓湾还要返回沱口阅读谱书,又要祭祀宗祠,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恐怕司机难得等,最好是乘班车去。他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与革成先生通了电话。他又把早班车发车时间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误车。我们告诉他,后天上午想请老家的部分宗台来会一会,吃顿饭,留个影,请他邀请寨山下他认为合适的宗台,并提前把人数告诉我们。他点了点头。 社保先生告辞后,我们又把到沱口阅读谱书的事商量了一下。由于时间紧,我们把阅读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即:序、先祖生卒时间、神保公以后的资料、其它。并进行了分工,到时各自按目标迅速寻找到有复印价值的东西,以便复印。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按照革成先生关于“晓湾现已改名湾头”的提示,乘早班车到了湾头。湾头座落在一个山脚,面前的土地好平好宽,可用“一马平川”来形容。革成先生还未到,我们便进了村子,看到各家门牌上都写着:“湾头村XX号”,又向村民打听这里原来是不是叫哓湾。得到的结论是:这里叫湾头,究竟以前叫不叫晓湾那就不知道了,没听说过。村民们还告诉我们:这里的住户都姓程,一家姓郎的都没有。我们有所狐疑,是不是革成先生搞错了?既然如此,在此多呆无益,等革成先生到了再说。于是我们便往村外走去,刚到村口,一个村民跑来叫住我们说:“这里有一位女老人可能知道,你们不妨去问问她吧。”于是在村民的引导下,我们到了女老人家。女老人70岁左右,披短发,上海人,对我们很客气,她告诉我们:“这里原来就叫晓湾。”问题得到了证实,我们告别出了村子。回头看了看村子的外观后,便往回走。边走边议:盛公五月而孤,是在外祖家长大的,他外祖家恐怕就是住在这里,他长大后就在这里居住了。这就要看他外祖是不是姓程。打开谱书一看,不对,是姓李而不是姓程。这种猜测错了,那只能是盛公长大成人后,选择这里居住的。我们都很佩服盛公的好眼光,选择这么个好地方来居住。此时我们觉得晓湾之行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只需选择一个地方撒土、取土就可以到沱口去了。革成先生也没有必要来了。我们决定打电话给革成先生征得他的同意后,便可开始行动。可电话老是打不通,我们只得朝公路方向走去。 我们快接近公路时,革成先生已乘车赶到了。他一下车我们就把想法告诉他。他说:“不不,要去看看郎家井。”我们又只好跟随他返回村里。 郎家井在村子的左侧,保存完好。井口与地面平行,干干净净的,井中清澈见底,凉气逼人。村民也陪我们一起观赏。据他们介绍,这口井的水很好吃,过去全村的人都在使用,现在大家都用自来水,就没有用了。但现在仍然可以使用,人们仍然叫它“郎家井”。我们提出要“饮水思源”喝喝“郎家井”的水的要求,一个村民就马上跑到自己的家里拿来了吊绳和水桶,熟练地把水打了上来。那水真好喝,我们每人都使劲地喝了一气。后来,革成先生指着井上面的地说:“这里原来有我们郎家的祖坟,我曾经来拜扫过。”一位村民爬上地埂,边走边指划着范围说:“过去这一大坝都是郎家的祖坟。”可现在一所坟也没有了,所见所闻,一股悲凉之气袭来,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尽管如此,我们根据他们的描述,便认定这里原来确有祖坟,而且祖坟还不少。虽然祖先灵魂所依附的外壳已不复存在,但祖先的灵魂还在,并深深藏于此泉壤之中,我们仍虔诚地在这里祭拜,并将所带来的泥土庄严地撒在这里,然后又谨慎地有如拾取宝珠似的取上泥土带上。临别,我们又再一次喝了那甘甜纯美的“郎家井”的水,再一次瞻仰那曾经是祖先墓地的风水宝地。 离开湾头,我们与革成先生一起步行返回沱口。路上我们无所不谈,在谈到郎文杰先生首倡修《郎氏通谱》问题时,革成先生说:“我已给他写过信,提了不少建议,不知他有何打算。看来这事不容易啊,难度太大了。”当我们对他这样一位80高龄的老人竟然有如此健康的身体感到不可思议时,他风趣地说:“是老天照看我,是祖宗保佑我。不然,你们会见到我的文章,会到这里来?”到了沱口,革成先生招待我们在其妹家进午餐。我们边吃边交谈,忽然革成先生的手机响了,接了电话,他说:“有病人等着我去看。吃完饭,我就不陪你们了,我去看病,你们到宗祠遗址看看。”临别,他又说:“我问问拉病人来的车能不能坐,如果能坐,我就通知你们坐他们的车回清华。” 分手后我们就向宗祠方向走去。这里叫屏山村,由沱口、岭下、屏山三个村民组组成,是连成一片的。在当地一位宗台的指引下,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宗祠的遗址的背后。这时革成先生来电话告诉我们说,再过半个小时就可以坐他们的车回清华了。我们来到宗祠遗址的前面,庄重地进行祭祀、撒土、取土仪式,围观的人也不少。郎日彬、郎百顺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位老的也正在修谱。”我们很高兴,便随他们前去拜望。我们进了一家屋子,这时我们才注意,老家房屋都有同一种模式:一进正门,屋内呈“凸”字形,凸头正面墙上张贴着图画、相片什么的,挨着在中心线上摆放着一张八仙桌,漆得锃锃亮。八仙桌的上方有两把椅子,其它三方是三条长板凳。凸底两侧,是生火做饭起居用的。“凸”字形内部没有隔墙。凸头前面墙壁左侧有一道门,是进入内室的。我们在八仙桌的长板凳上坐下后,一位老先生就拿着一卷图画纸进来了。他叫郎广欲,60多岁,身材高大,是一位退休教师,知识渊博,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原以为我们是九虎入云南的,便拿出一张大画纸展开给我们看,是瓜瓞形式,排列整洁,美观大方。我们说明我们不是九虎入云南的后裔,而是神保公后裔,他又拿出另一张大画纸展开给我们看,我们迅速找到神保公名下的有关记载仔细一看,与民国五年版无异,看来也是取材于民国五年版的。我们把民国五年版与镇雄版有出入的问题告诉了他,并希望他能帮助我们寻找有关老版本的谱书。他说,找不到了,县城里一位退休教师倒有一部,不过也是民国五年版的。这时革成先生来电话催我们上车,但我们的谈话仍在继续。广欲先生谈了立志修谱的决心和信心,他说:“这里迁到日本的、韩国的、新加坡的都有,我准备与他们联系。我还准备到你们云南跑一趟。”我们说欢迎,并建议他多约点人一起干,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还邀请在座的宗台明天上午到清华一起叙叙。 临别,郎日彬对我们说:“如果你们回去找不到车,这里可以找。”我们说:“我们先去看看找革成先生看病的车走了没有,如果走了再联系。”我们走出村子,发现那车已走了,便向公路走去。等了好久,无来往的车辆,便电告郎日彬,请他找车。不久郎日彬又来电询问我们所处的具体位置。我们四处看看没有标的物,只说正在公路上。好个郎日彬,他担心我们“漏网”,采用了前后夹击的办法:他让司机开车从后面追赶,自己骑自行车从前面赶来拦截。正好三方会齐便上了车,我们好感动啊。赶到清华,天快黑了,我们抓紧时间到寨山下祭祀宗祠,并完成了撒土、取土任务。 十一月二十七日。革成先生来得早,他带来了民国五年版,我们选择了从1至53世祖及神保公以后的资料作为复印对象。革成先生就带我们去复印,中途他有事就离开了。当我们复印好材料返回住处时,郎广欲先生已经等候我们好久了。 广欲先生向我们边画边描述屏山宗祠的情况,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们问:“屏山宗祠是否立得有郎芳声所题的‘源远流长’这块匾额?”他不假思索地说:“有!”我们再次提起康熙二十七年版及其以前的版本时,他仍然摇头:“找不到了。婺源博物馆也可能没有,不过还是去看看好。最好到上海图书馆去查一查。”他还说:“上海有一个宗谱研究协会,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了解一些情况。不过,我只是听说,我没有去过。”这时我们已经有了去上海的念头。 等到革成先生等人会齐,便在我们下榻的浙源饭店共进午餐。赏光的有:寨山下的郎社保、郎秋元、郎亮生;屏山的郎革成、郎广欲、郎锦水。由于两代问题还没有定夺,暂时还不好按老幼尊卑关系来称呼,只好互称宗台了。大家都不行外交礼节,因为都是自家人,在唠家常,在吐心曲,所以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显得自然和谐。在谈到合影的具体地点时,社保先生提议在寨山下的宗祠门前合影最有纪念意义。大家都赞同,并让郎锦水负责联系摄影师。 饭后,我们一起到寨山下宗祠门口和双河桥上(以寨山下为背景)两处合影留念。照片印出后,大家拿上便陆续告辞了。 革成先生留下来为复印件逐一清点页码并加盖了自己的印章,又在复印件的扉页上提上自己的意见。我们也把随身携带的镇雄《郎氏通谱》以考证组的名义赠送给老家的宗台们作个纪念,并请革成先生保管。革成先生赠送了礼物给我们,还把自己的心血结晶《问世初集》和《婺源楹联》等资料赠送给理事会。革成先生宣布:“今晚我就不走了,要好好与你们聊聊。”我们高兴地拍手。 晚上,我们围绕两个版本记载有出入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革成:你们下一步打算如何行动? 我们:去上海。仅凭民国五年版和镇雄版这两个版本很难作出选择,如果能找到嘉靖八年版、嘉靖三十年版、万历年版、康熙十七年版、康熙二十七年版,或者这五个版本中其中的一个版本的原版来参照,问题就就不难解决了。我们想去上海碰碰运气。 革成:对对对,找到老版一参照就好办了。在婺源是找不到的了,因为我们这里历来是这样的:新版一问世,老版就要全部烧掉。 我们:啊!原来是这样,看来希望不大了。当年宏声公来抄录老谱的情况你听说过吗? 革成:没有。 我们:其胞弟郎芳声所题的“源远流长”的匾额,在屏山宗祠你看到过吗? 革成:看到过。 我们:恕我们直言。我们想对民国五年版提点粗浅的看法。 革成:请讲。 我们:我们认为,民国五年版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比较明显:第一,神保公是洪武十三年随沐英到达西南的,是十大指挥之一,这是我们当地有口皆碑的事实,民国五年版却只字未提;第二,民国五年版记载文公、武公失考,而我们考证组就有文公的后裔;第三,在献公名下,记载有“生子永忠”,永忠的兄长世忠却未载入,而我们考证组就有世忠公的后裔;第四,在声字辈里,没有秀声公的名字,而我们的代理事长就是秀声公的后裔。由此可见,民国五年版也是有疏漏之处的。 革成:这确实是个问题。 我们:不过,问题不在民国五年版,而在于嘉庆八年版。而嘉庆八年版是在宏声公来婺源之后21年所修,所依据的版本,必然是康熙二十七年版,而两版之间的间隔年限是115年,章页的残缺,字迹的模糊等诸多问题不会太少。而嘉庆八年版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版本,以后版本只是照录而已。 革成:这种推理有道理。 我们:当然这是我们的粗浅的看法,怎样定论那是理事会的事情。 议了正题又转入闲聊。 革成:你们的“墓谱工程”把墓放在前面,是不是把建墓看得比修谱重要? 我们:也不是这个意思。当初是以建墓发动族众的,没有计划修谱。后来根据形势发展和族人的要求才增加修谱的内容的。因此才把墓放在前面,并不是修谱没有建墓重要。 革成:啊,原来是这样! 我们:请教革成先生,老家对同一个姓的人是不是都称“宗台”? 革成:对呀,“台”就是表示尊敬。你们那里是怎么称呼的? 我们:称“家门”。(同时翻开镇雄《郎氏族谱》找到《告众家门书》给他看。) 革成:(看完后便改口称呼我们)家——门—— 我们:(回敬)宗——台——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革成先生被一辆面包车接去看病了,我们就进城吃社保先生的次子郎辉的喜酒。社保先生陪我们坐一桌,并把我们向客人们作了介绍。我们品尝着美味可口的老家风味,心里乐滋滋的。老家办喜事不兴挂簿子,是送红包。商店有专用的红包套销售,买了来装入礼金,封口,上款写明祝贺对象和事由,下款写上祝贺人的姓名,不写礼金数目,直接交给主人。主人对发出请帖者包车前去接,我们就是坐这样的车进城的。快散席时,每人还发得一件喜糖。喜糖由大小两包组成,在封口处,紧紧粘贴在一起,其含义不言而喻。 辞别了社保先生父子,我们又打车到时博物馆,还是没有开馆。仔细打听,馆内工作人员说,刚迁馆完毕,要举行开馆典礼了,过几天再来。这又让我们傻了眼,只好乘车到景德镇。 十一月二十九日。几经周折,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景德镇市档案馆,想查阅芳声公的有关资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档案馆正在搬迁中,清代以前的资料要老馆才有。究竟能不能查阅,要问馆长。我们又找到馆长,馆长说,要五品以上的才有,也不多,还只是明朝才有点。我们揣度,芳声公只是一个同知,可能不会达到五品,况且又是属于清朝,看来是无望了。我们只好在瓷都街上转悠。打听打听“郎窑”,人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晚上乘火车到黄山。 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游览黄山。 十二月二日。乘汽车到杭州,受到郎启波岳父一家的热情款待。 十二月三日。在郎启波岳母的陪同下,到浙江省图书馆准备查阅资料,不料也未开馆。只好游览了西湖、岳庙、灵隐寺等名胜。 十二月四日。乘火车到上海。到了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说明来意。他们说,云南郎姓的家谱这里没有。我们说,凡是郎姓的家谱,只要有完整版的我们都想查阅一下。他们说:“只有浙江萧山的郎氏族谱有一本,是第五卷,其它的没有。” 我们听了很扫兴。工作人员见我们惘然若失的样子,急忙忙安慰我们,便拿出一大摞书籍来让我们看看是否有可取的。我们只好在大量的资料中把有关“郎”的内容复印了一些带回来研究。 十二月五日。我们四处打听、寻找上海宗谱研究协会,未能如愿,只好到外滩逛了逛。 十二月六日。我们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乘火车到湘潭。 十二月七日。上午到韶山瞻仰毛泽东主席的故居。无意中,发现在一个亭子里有各姓氏来源的资料出售,封好的。我们迅速查找,确有《郎家姓来源》,高兴极了,买来打开一看,价值也不大,叹了口气,只好带回来研究。下午返回湘潭。晚上登上到贵阳的火车。 十二月八日。上午到贵阳。下午坐汽车到罗甸县城。 十二月九日。坐汽车到逢亭,再打摩托到井交。当晚在郎秀文家与当地家门会面。通过交谈,得知他们是从白鸟过路人迁来的。来的祖人叫郎不然(苗语音译),改姓杨,苗族,现已恢复郎姓。他们很希望帮助他们找到根。我们便按瓜瓞形式把他们从郎不然起到现有人口止,做了记录,答应回来向理事会汇报了再说。 十二月十日。返回贵阳。这次井交之行,本与这次考证无关,不过,事前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那里的族胞寻根心切,并征得代理事长同意才去了解情况的。 十二月十一日。到镇难。 十二月十二日。回到家里,并将返回的信息报告了代理事长。 十二月十三日——十七日。对江南之行进行回忆、梳理。 十二月十八日。我们集中向代理事长作江南之行的口头汇报。并对定性问题发表看法。大家认为,在没有老版本的原版作参照的情况下,在民国五年版与镇雄版之间很难作出抉择。虽然康熙二十七年版具有权威性,但镇雄版又不是直接取材于宏声公的手迹,中间难免有错讹之处,最好找到宏声公的手迹来作参考才好作定论。于是决定再赴贵州水城寻找宏声公当年抄录老谱的原始手迹。 十二月十九日——二〇〇八年一月九日。查阅资料,分析研究。 一月十日。赴贵州水城二塘找到郎文化,说明来意。郎文化说,他因年纪已迈,已交给儿子保管了。现在儿子又出去打工了,要等儿子回来才能找得到。我们只好提出:“等你儿子回来得到宏声公原始手迹的谱书后,请你把它复印出来邮给我们,怎么样?”他慷慨地答应了。 一月十一日。返回家里。其中,白鸟朱家沟的郎学康在赫章遇到我们,就主动包车送我们到镇。 一月十二日——三月二日。继续查阅资料,分析研究。 三月三日。收到贵州郎文化于2008年2月3日从二塘邮给我们的关于宏声公手迹的复印件。 三月四日——六日。重点对宏声公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三月七日——十四日。起草《江南老谱考证报告》。 |
|||||
|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
|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
| 最新热点 | 最新推荐 | 相关文章 | ||
| 江南老谱考证组婺源行留影 致郎革成先生的信 江南老谱考证报告(二) |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网站公告 | 管理登录 | | |||||||||||||||
|
|||||||||||||||